|
白癜风特效药 24小时,或许是重复着昨日平淡的普通一天。 但有时,也可能是生命剧烈的转折点,是高度浓缩的跌宕,是回顾一生中无数个「一天」时,仍然会精准翻涌的记忆。 这些镌刻在记忆中久久不会褪色的「一天」,便是人们活过的印记。 这里是视觉志推出的全新栏目——《24小时的朋友》。 栏目将用纪实的手法拍摄普通人不普通的24小时,褪去时间、秩序、人际隔阂的外衣,真切地挖掘人生的赤裸和粗粝,寻找活着的真相和生命的力量。 上一期我们和结束5年北漂生活的农村女孩娜娜聊了聊,而这一期我们走进北京松堂关怀医院——一家收治临终病人的医院,和护工李大姐做了24小时的朋友。 李大姐是四川人,今年47岁。 1999年,她经熟人介绍,从老家来到北京,进入松堂关怀医院工作。 23年来,她照顾过上百位临终者,有正值壮年的癌症患者,也有年事已高的临终老人,看护时间最短的不到半个月,最长的能有8、9年。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,李大姐需要24小时无间断地陪护在病人身边,每一秒都可能和「死亡」打照面。 我很难想象,一个人如何在如此压抑而沉闷的氛围中日复一日地工作?临终医院里的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? 而24小时过后,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对「衰老」和「死亡」的狭隘理解,也终于揭开了蒙在「临终关怀医院」上的黑色面纱—— 或许,令人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,而是我们对死亡的固有想象。 以下是我在松堂24小时的观察—— 临终医院?真「晦气」吗? 凌晨4点,松堂关怀医院已经开启新的一天。 深秋清冷的天气、车辆寥寥的公路让这座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医院更显寂静。 在三楼病房见到李大姐时,她刚整理好床铺。因为要全天候在病房内「待命」,所以松堂的护工没有单独的宿舍,而是和临终者同住。 他们遵循着「反常」的生物钟,在几乎不存在个人隐私空间的状态下生活。 但在决定当护工那刻,李大姐就做好了心理准备,这么多年来,也早就习以为常。 李大姐照顾杨奶奶 她目前看护着一对老夫妻——蔡爷爷和杨奶奶。每天早晨在打理自己前,李大姐需要先给老两口洗漱。 蔡爷爷74岁,5年前突发脑梗,幸好治疗及时,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后果,但从那之后,他的右手就无法灵活使用,腿脚也越来越不利索。 杨奶奶在上半年意外摔倒,导致大腿胫骨粉碎性骨折,由于身体状况的限制,医生不建议立刻手术。 自此,奶奶的活动空间就被框定在一张单人床上,两位老人在家的生活也变成一团乱麻。 「没有子女照顾吗?」 有的。 两位老人的独生女蔡阿姨会定期上门探望他们,但她的小外孙女刚上幼儿园,需要人帮着带,蔡阿姨没有足够精力兼顾老人和小孩的生活。 家里也试着给老人请钟点工,但钟点工能做的事同样很有限,清洁完屋子、衣服、做完午饭就已经尽了这份工作的职责。 因此,吃了上顿没下顿、没人帮忙及时注射胰岛素的状况在两位老人的家中频频发生。 生活的失序在外貌上也有很大体现。 蔡爷爷说,那段时间自己的头发长到能盖住脸,「都看不出人样了」。 家庭无力承担繁重的看护工作,成为全家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 李大姐陪蔡爷爷聊天 于是一个月多前,两位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进入松堂关怀医院。不舍和纠结肯定会有,但这个选择至少能让老人体面地度过晚年。 其实,像蔡爷爷和杨奶奶这类生活很难自理,但神智清醒、没有重症,甚至有时还能借助轮椅活动的老人不是孤例,不过这类人群在医院也绝非多数,他们只占三成。 大多数临终者的情况更为复杂,年龄跨度也很广。 几个月前,李大姐曾照顾过一位40多岁的女性,刘女士(化名)。 刘女士是癌症患者,脑部长了难以摘除的肿瘤,早年间和丈夫离婚,有一个20来岁的孩子。她平时不爱讲话,但很清楚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,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。 某个夜里,刘女士突发高烧、离开了人世。因为走得匆忙,她没能见到孩子最后一面。 「和孩子好好告别」成了她在生命尽头未遂的心愿。 松堂关怀医院的某间病房 而在医院的一楼走廊深处,有一个清静的小房间,里面摆放着十张婴儿床。 这是松堂的婴幼儿病房,里面收治过的孩子最大不过三四岁,最小只有几个月。 很难想象,这么年幼的生命会和「临终者」这个称呼联系在一起。 走到房间最里侧,你会听见重重的呼吸。 发出声音的人是一个脑积水的小男孩,他的头相比普通小朋友膨大了几圈,这是脑积水的典型病征。 但如果你向他招手,或者和他讲话,他并不是毫无反应,他会摆动小手回应。 他是能感知到外界的鲜活生命,这一点和任何普通小朋友无异。 被送进松堂的孩子大多像他一样,天真、可爱,却有着难以治愈的先天缺陷。 朱朱也是,他刚出生几个月就被送到这里,现在已经一岁半了。 乍一看他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,但因为脑梗,他的脑袋始终只能倒向一边,随着年纪增长,这种状况会更严重、更明显。 他的本名其实不是朱朱,准确来说,朱朱没有名字,他在登记簿上的姓名是「王某之子」。 松堂关怀医院的婴幼儿房 早晨8点,医院后面开进一辆殡仪车。又一条生命即将完成告别仪式,去往另一个世界。 而这样的场景,在松堂太过平常。 李大姐仍在3楼病房里工作,走廊一侧的某间病房里,时不时会传来临终者疼痛的呻吟。 松堂这天的早晨,无疑是灰暗的。 衰老的不可阻抗,病痛和死亡的无差别攻击,让人喘不过气。 直到阳光点亮病房里的玫瑰假花,才显出一抹颜色。 看见TA姓名 「哥哥姐姐,你们要吃果丹皮吗?」 这是彬彬逢人就说的话。 上午9点,医院集中活动的时间,彬彬穿着一件绿色外套,在一楼活动室外徘徊。 她背着大挎包,包里放满「奇珍异宝」,随手就能掏出一个绿色系眼镜框搭配外套。 护士姐姐看见她,叫她进活动室玩。彬彬接过护士递来的话筒,在大家面前大大方方地唱着《同一首歌》,尽管她只会循环前四句。 唱歌之外,彬彬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医院里走来走去,和不同的人搭话,换不同的衣服。每天都能「日行两万步」。 她很快乐、也很纯真,生活得无忧无虑,和小朋友一样。 但其实她的生理年龄已经38岁。 彬彬在活动室外 彬彬11岁时,她的妈妈突然走失,而彬彬对世界的认知也从此停滞。 后来,爷爷奶奶一直照顾着彬彬。两位老人离世后,叔叔、婶婶又接过看护彬彬的接力棒,直到他们也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,才把彬彬送到松堂。 直到现在,叔叔、婶婶还是会经常来看彬彬,给她带零食、水果和新衣服,松堂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知彬彬的喜好,时不时会送给她一些帽子和小配饰。 彬彬是精彩的,是被爱包围的。 在松堂的很多「临终者」也一样,他们有姓名、有个性,绝非一群苍白无望的行将就木之人。 中午12点,医院大堂举办了一场小小的生日会,生日会主角是89岁的武奶奶。她脸上的皱纹很引人注目,像「猫咪胡须」。 陪伴在武奶奶身边的是她的亲人,儿媳妇在现场掏出口琴,吹了一曲《祝你生日快乐》。围坐在武奶奶四周的,是她在松堂医院的三个好姐妹。 这「四朵金花」在院子里活动时,喜欢坐在一起聊天。不过,虽说是「聊天」,但其实大家的交流方式就是「各说各话」。 在她们的世界里,比回答更要紧的,是有一个舒适轻松的环境去表达自我。 「猫咪奶奶」武奶奶 分蛋糕时,一个奶奶行色匆匆地从大厅经过,她穿着一条红紫格子纹的裙子,端着洗脸盆快步往浴室赶。 她是花花,每天中午都要洗个澡才舒坦,问她今年几岁,她会回答「刚满18」。花花肚子很大,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里面装着宝宝,有时装了2个,有时装了5个。 「花花为什么这样说」是大家心里的一个谜。 这些可爱又独具特色的「人物小传」,松堂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。 即便是「已逝者」的故事,他们也如数家珍。 李大姐曾谈起她照顾的第一个病人,一位60岁的盲人孙大爷(化名),从没结过婚,也没有子女。 孙大爷心脏出了问题,送他来医院的人是单位的同事。 在松堂生活的三个月,他不想依赖导尿管,大小便会让人扶去卫生间。会自己去打饭,只是吃完后需要人帮忙刷碗。 他尽力维持独立和体面的生活,直到不得不卧床那天。 李大姐当时24岁,虽然有36岁的年龄差,但他俩沟通一直都很愉快。 和孙大爷相处的时间里,李大姐印象最深的是两人出去散步的日常。 当时松堂还在玉蜓桥附近,医院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鸟市。每当孙大爷说想出去溜达溜达,李大姐就会牵着他到那边去转悠,买点小零食。 最后,孙大爷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,医院帮忙安排了后事。 医院凉亭 「挺心疼的,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憋着话没说。」 时隔多年,李大姐仍然记得那时的感受,「像失去朋友一样的心情」。 这种伤感并不会因为经历次数多而减淡。 护工、护士、医生、药师包括志愿者依然需要在一次次的讲述、宽慰和告解会中将负面情绪排解出去。 而「记住」,则是疏导完悲伤情绪后的重要命题。 在松堂,有一本志愿者整理的相册,里面的人物,都是曾在松堂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临终者。 或许生者无法阻挡他人死亡的进程,但只要在脑海中留存关于「逝者」的记忆,他们就会成为生命长河中一颗始终闪烁的星星。 我们可以这样坚信。 关于死亡关于微光 下午15点,松堂院子里的喷泉,闪烁着波光。 还能活动的病人下楼到院子围坐在一起,听听音乐,做做保健操,和周围的人聊聊天,大爷们可以在院子里找护工大叔舒舒服服地剃个头。 临终者最常发生的问题之一,是感觉自己不被理解也没有人可依靠,会很孤独。 因此下午聚在一起的两三个小时,是让大家保持身心愉悦,维持社交关系网的重要时间。 也是这时你会发现,在临终者之间,「死亡」呈现出复杂的「众生相」,而不是统一的恐怖模样。 松堂下午集中活动 蔡爷爷很开心,跟伙伴们大谈邓丽君的一生。 聊历史、诉说他年轻时当采购员的经历,是他来到松堂后最重要的消遣之一。大家也很捧场,虽然听了很多次,但每次都还是能当成头一回来听。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,要高高兴兴地走完」。 对于死亡,蔡爷爷的态度很乐观。 陈奶奶也现身了。 松堂院墙上有一条标语是「我要活到120岁」,她是整个医院最接近目标的人。 她今年104岁,头发花白但腿脚依然好用,甚至还能帮80岁的老人推轮椅。 她已经活过了一整个世纪,对于「死亡」已经没有恐惧,只有坦然。 杨奶奶依然会难过,不是为「临终」难过,是为自己卧病在床,不能「体面地活」而难过。 她时常讲起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,唱点小曲儿,教大家说上海话,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。 李大姐会握着她的手宽慰说,「别难过,现在不是好好的吗?」,杨奶奶总会回答,「这是开心的泪水」,幼年的时光是她记忆中的金子。 彬彬换了一条花裙子、一件小洋装外套,朱朱坐在婴儿车里,打量着周围的人。 对他们来说,「生命」「死亡」或许只是朦胧不清、难以理解的词汇,最重要的只有当下的快乐。 有两个大爷相谈甚欢,护士告诉我左边的大爷过去是在清华任教的老师,右边的大爷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,被救回后进入关怀医院,和「清华老师」成为挚友。 对于「死亡」,两位大爷或许有更为独到的理解和反思。 陈奶奶和朱朱的「世纪同框」 而对李大姐和松堂的工作人员来说,这份工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是,他们逐渐认识到「死亡是一个自然发生、难以逆转的生命进程」。 这和我们长久以来,对死亡的既定叙事相悖。 我们的文化总是在排斥死亡、恐惧死亡,费尽心思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中,寻找延长生命的更好方式,放弃治疗有时被看作是懦弱的选择。 哪怕代价是让老人、病人承受更多不必要的痛苦,让「生」的体验大打折扣。 正如阿图·葛文德医生在《最好的告别》中描述的那样—— 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,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,我们的末期病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。 但实际上对临终者而言,最重要的或许不是「强制逆转死亡的进程」,而是「尊重生命易逝」,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照顾。 这也是松堂关怀医院贯穿始终的理念—— 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是延长生命的最好方法。 至少让生命最后一段旅途在爱、诗歌和温暖中度过。 那么,承认「生命有期限」「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」,对生者的意义是什么呢? 我想起某社交平台曾发起一个话题是#写给天堂的你的一封信#。 参与话题讨论的人们纷纷发布信件,去纪念亲人、爱人、友人,包括陪伴了自己一程的小动物们。 书信讲述着TA的一生,写信人和TA之间那些闪光的回忆,以及希望TA在天堂能开开心心,常来梦里看看…… 好像在书写的过程中,那些没来得及说出的告别,都有了寄托和出口。 而由此衍生的,还有一批#天堂回信#,其中一封是匿名网友以小狗的口吻写给了伤心的主人,书信内容是—— 亲爱的主人: 我是小狗 我很爱你 所以当我发现 你不爱自己的时候 我很难过 爱你的小狗 图源微博@小狗的口袋 所以,或许看见并走近「死亡」,并不是剥夺人们悲伤的权利,而是创造一个情绪的出口,提供相互疗愈的树洞。 不再执着于对生的无止尽追求,而是去思考死的坦然和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体验感。 而当人们真正开始接受「死亡」,才能更好地珍惜「活着」的日常。 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对「临终关怀」和「死亡」的认知和故事,我们下期再见!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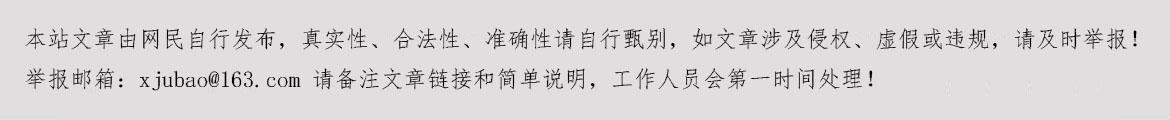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• 新闻资讯
• 活动频道
更多




